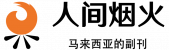《信的告白》
赖国芳
中国电影《老炮儿》的主角是六爷。六爷在年轻时横行北京,曾经风光无限,有自己的原则和江湖规矩。如今,六爷已成老炮儿,成日提笼遛鸟,无所事事,在胡同里偶尔为街坊仗义执言。时代的巨轮无情碾过,那套老规矩已逐渐行不通。某日,他与老相好约炮,竟连炮杆儿也提不起来呢。
六爷的儿子刮花官二代的蓝波基尼,被非法囚禁。老炮儿勉强筹足两千人民币,想摆平此事,却被新小炮儿们着实羞辱了一番。六爷和过气江湖朋友,碰上新世纪中国的金钱至上和官商勾结,一败涂地。在重重打击下,老炮儿们尊严尽失,心头郁闷,决定以老方子解决此事。结尾,虽然明知必败,六爷仍手持军刀,在寒冬冰冻的湖上,发狂扑向如群狼饿虎的恶霸。
这是一个隽永的小说与电影题材。一群被时代遗弃的小人物,活在社会边缘,依靠老规矩旧知识,与新世界周旋。最后被逼上梁山,是妥协?或孤注一掷?便成就电影的张力。
长堤两岸,也有老炮儿。
2015年的记录片《我们唱着的歌》,把新谣与“末代华校生”挂钩,跟南大诗乐同归一源。上世纪八十年代,李光耀政府关闭南大,改制教育,华文中学在新加坡消失。华校出身的中学生,来到以英文授课的初级学院,面对强势语言,霍然变成弱势群体。他们把心中的茫然,以及对华文的不舍,通过音乐抒发,创作了一首首青涩却真诚的歌曲。
恰在同时,我在北马修完六年中学,申获亚细安奖学金,到新加坡国初攻读高中。当地学生只修四年中学便考O水准,我因此比同级生年长两岁,且是来自“州府”的乡巴佬。然而,两地华校生气质相通,在学习上面对的语言障碍却相同。比起来自大马英校的同侪,我与这群末代华校生,更容易打成一片。
82年尾,初院举办歌曲创作比赛。我把一件半成品稍作整理,浇上离乡背井的新感触,写成《信的告白》,获得冠军。同时期,校园歌曲开始在各学院涌现,众多歌手与小组,如华初的梁文福,裕初的巫启贤等等,皆纷纷崭露头角。84年初,新谣第一张合集《明天21》出版,《信的告白》被选入。
红尘滚滚,苍老了容颜。孩子们长大,都不爱讲中文,遑论读中文书。三十年间,新谣从全盛走入沉寂。作者封笔,歌手封麦,或转战企业,或洗净铅华。回忆淡化成历史。
2014年,李显龙总理在国庆献词里,出人意表地哼起“细水长流”。翌年,适逢SG50,“年少时候/谁没有梦”在岛国各角落响起。官方与民间举办的新谣演唱会,几乎场场爆满。年届半百的歌手,粉墨登场,再度跃上新闻版面。同龄的观众,买起价格不菲的入场劵,毫不手软,仿佛要对过早流逝的青春作出补偿。
《信的告白》被重新发掘。这个年头,人们不再写信。500里路,一趟廉航即可搞定。当年穿山越水的离愁,或许已成永恒的遗憾。然而,世事就是如此吊诡和荒谬。这首歌骑上风潮的翅膀,原唱“清泉小组”多次被请上台,一些年轻人,包括一名小女生,也选唱此曲。我被告知,此曲容易上口,竟成了新谣的“启蒙”曲之一。
其实,当年孕育新谣的土壤已不复存在。当代的狮城年青人,虽然受过更好的音乐训练,却再无梁文福驾驭中文的能力,或巫启贤拒绝死读书的勇气。2015年,弹唱人餐厅在数开数闭后结业,标杆性的“海蝶音乐”被大陆公司收购。那场场座无虚席的演唱会,更像是同学会,久别重逢,心情激动,叽叽喳喳热泪奔腾。待多年压抑的话说完,政治功能被消费殆尽,热潮便难以为续。
长堤对岸,幸无华教断层的剧痛,“马谣”也未曾经历大起大落。然而,时代更替,坚固的烟消云散,神圣的已被亵渎。6字或7字辈人,胸中的中文墨水和旧价值,似无用武之地,怕也与六爷同感身受吧。
就不知长堤两端的小说家或电影人,有无功力刻画老炮儿的屈辱与挣扎,以及飘雪冰湖上慷慨就义的凄美呢。
本文所提及歌曲视频
可点击此处观赏
资讯:
《信的告白》词曲:赖国芳
2016年3月15日 马来西亚 星洲日报 《曲中人生》系列
摄影:丁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