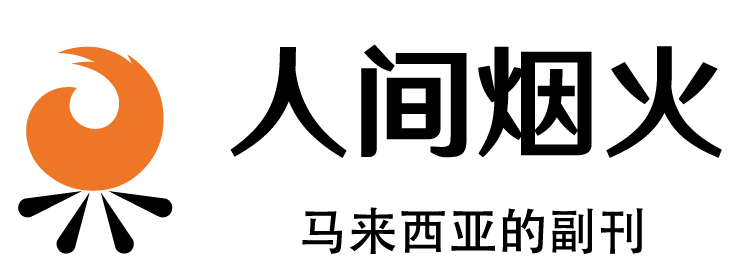张雨
小时候,外食的机会不多。多数由外公带着,我们才有机会四处寻找美食。父亲因为收入不高,只满足三餐糊口,幸好有外公和外婆带着四处见识,我与妹妹才不会变成井底之蛙。
常常是在火锯厂当经理的外公,趁傍晚与人在新加坡的老板越洋电话会议后,开车载着外婆来我家,把母亲、我和妹妹带去寻找美食。印象深刻的其中一个美食是炒粿条。
那年代,镇上某戏院前有个档扣售卖炒粿条,生意火热,别人关了店门的店铺,五脚基走廊就是档主的另类美食天堂了。虽然只是几张塑料桌和椅子,但总是座无虚席。有时排队等打包的人也多,排成一支足球队的人数,当中还有几个是印裔同胞。
档主用木碳燃烧,炉火旺盛,加入新碳后,经常有响亮的爆裂声,火花四溅,看得人心振奋。初夜半昏暗中,象征着温暖的火温,扣人心弦。锅里集结先后顺序下去的食材,由简入繁。自爆香蒜泥开始,后到的肉片或血蚶翻炒的同时,一匙接一匙的调味剂填加入锅里,火温使食材释放香味与炊烟袅袅升起,人间烟火就在眼前。
香气引诱原已蠢蠢欲动的舌头,口液促使不由自主地往肚子里咽。美食当前,多数人也不掩饰,那是对美食最真诚的敬礼;档主将粿条下锅,随即勺上黑酱油,铲子翻过,铁敲铁声响起,大伙知道距离可以食入肚子会更近一步了,再看着档主如耍杂技的手势——敲壳、下蛋和抛壳的数回顺序演出,旺火烧到半焦的粿条与蛋相遇后,来点水花洒落,缓解热恋中的缠绵悱恻。炒粿条的主配角都入戏对味后,一盘油亮油亮的赤黑几经撕杀却分不清的粿条盛餐就呈现,档主为嗜辣的顾客填加自制的峇拉煎辣酱,食客没有味蕾不被锁定的,就这样档主培养了无数的回头客,久不久就会回来光顾,以解口羽之瘾。
母亲是那种凡吃过一次后,就会想自己试炒的人,这就是母亲的神奇之处。往后的日子,我们总会不定时地尝到母亲的手艺。
母亲将炒粿条模仿得似模似样。母亲使用炸过的猪油炒粿条,除了增添顺滑感,更是香气满满。盘中加上猪油渣碎块的粿条,更是叫我爱不释手,通常可以续盘无数次,直到母亲喊停为止。即使是母亲不在后的多年,我依然常会想念着母亲和炒粿条。
日前,二女儿真在古来试驾新车的午后,找到古来大街已传承四代的炒粿条档。档主挂上的纸皮写着:营业时间11至3点,星期五、六和日三天。生意好到不得了,我们一家中午1点抵达,找个位子,只能抢到两盘炒粿条。
吃着炒粿条当儿,向太太说着母亲的炒粿条故事,找到了母亲的味道,但就是份量太少。我们说的话,被隔桌一个衣衫整齐的老人听到,他向我们边点头边微笑。
之后付款时,从主持炒粿条的男士口中知道,那个人就是前档主,是他开创出来的事业,虽然“金铲高挂”,但依然每天坐镇。
我对档主说:“这可是当年的网红哟!”
档主也幽默地回应:“有阿公在,就是品质保证。”
Photo by Advocator SY on Unsplash
支持作者
喜欢这个作品?请略表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