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家杰
在求学之前,我不曾有故乡。我生长于家族的乡土之上,从小学开始,听见同学们说新年要回家乡、说要 “balik kampung”的时候,我往往无感。“家乡”一词之于我,就像因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而相识相伴数十年的糟糠之妻,全然没有爱恋之意。随着时代的脚步,这块土地遭到了时代洪流的冲刷,如芸芸乡土一般;曾经孕育的生命乘着新世纪的海浪到新的土地冒险扎根,如上世纪到南洋谋生的壮年一样。直至如今到外坡上学,才品到了几分家乡的滋味,故土的风景与气味总是游子魂牵梦绕的感官体验,或许上大学也是重新审视家乡的捷径之一。
上学三年,有两个重要日子是必须回乡的,其中之一便是春节,而且一待就是五至十日,吃饭、拜神、接待亲戚简直应接不暇,特别是拜神和拜祖先,前一天就得将隔天或者当晚的神料和供品捣鼓好,到点了一拜就是两、三个小时的“工作”。当然这也是亲戚们回乡的日子,但上述工作都不会劳烦他们,至多也是随着上三支清香,倒是我们一家才要花上几天时间既接待又祭拜。人们常说家乡的味道就是由亲戚朋友的嘘寒问暖组合而成的,但春节的叙旧和嘘寒貌似都在讨吉利,堆砌的关心和张嘴就来的吉利话反倒少了些“人味儿”,说好不说坏,毕竟暖阳多了也会灼热起来。说来诡异,让他们在我闻到“人味儿”的时候却是在清明节,另一个必须回乡的日子。
我们的扫墓又叫拜山,是中国华南地区的俗语,随着上个世纪跟着先辈一同下到了这片南洋半岛。不过我从小的认知是因为我们要爬上义山拜拜,所以才叫作“拜山”。华人义山在东南亚华人族群中拥有独特的地位,更多地象征一种认同与联系,相比起灵骨塔,义山的萧瑟与凄凉更能显现对祖先的敬畏,踏着泥泞的山路、跨过无人问津的孤坟、拔开蛮横生长的野草比起脱鞋就能进入有冷气的灵骨塔更能体现扫墓的“扫”字。在翻山越岭寻墓的时候,或许是血被煮熟了,随着汗水和疲惫,亲戚们的话语才逐渐有了温度,也就扫墓时才会想跟他们聊上两句。
死亡最能切割出家乡的温度,因为死亡是回忆的召唤,提及逝去的某某,总会冒出无数形象和往事,而“家乡”正是无数回忆的堆砌。小辈们在除草、清理的时候,长辈都会成群围在墓旁聊天,从与墓中人的关系与回忆、自己的近况与喜怒哀乐、到身边人(或新闻上的人)的奇妙或荒唐际遇,从墓内到墓外,放眼自身到回顾世界,只有切身实际与大而无当的交叠才会是生活的气息。我在新年时总喜欢躲在家乡的房里听着烟花爆竹声与麻将声入眠;在拜山时就喜欢一边清理打扫,一边听家人亲戚的谈笑风生,祖辈西去许久,早已不会有“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惆怅悲凉,反倒是除去新年,奶奶最期待的日子。
唯新年和清明才会让游子们排除万难赶回家乡。新年过于制式和墨守成规反倒带不出“回乡”的情感,多是完成年度任务的感觉,作为多年的“守乡人”,奶奶看似更期待清明节拜山,清明节未必会是假期、未必在周末、未必是天气晴朗的日子,事前还需要准备供品和神料,但种种困难反倒加深了 “家乡”的重量,才能感受到家乡之于他们的感情与温度,换句话说是对家乡祖先的“诚意”。对家乡的牵挂与拜山的诚意有着某种同质性,都是在茫茫人海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根,回忆起港剧中常有的那句“有乜野拜山先讲!”都随着感知的改变而被解读出了粗鄙中的温暖。
Photo by Kelvin Zyteng on Unsplash
支持作者
喜欢这个作品?请略表心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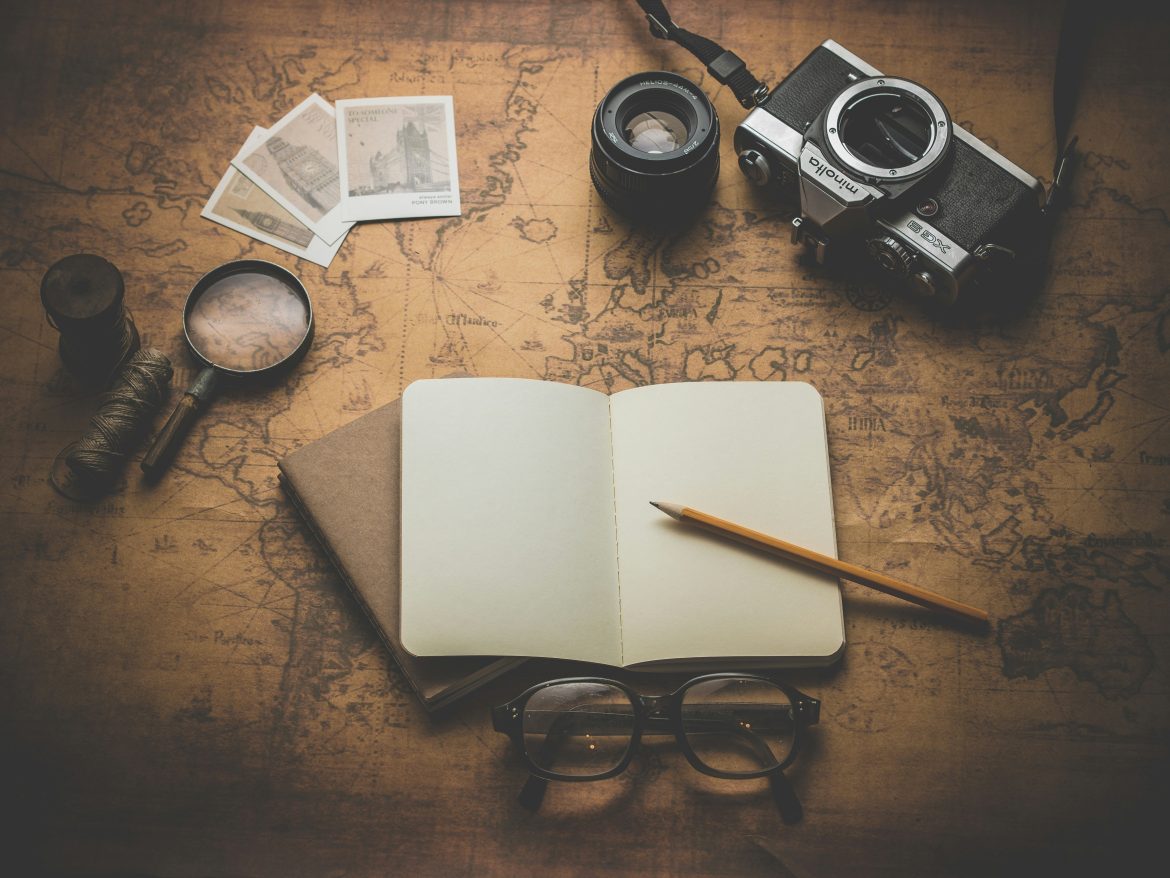 为鼓励创作者开启创意之旅,人间烟火在2025年第一季推出起步赞助计划,为符合条件的公众号提供一次性支持:
RM100 赞助(首批20个公众号)
RM250 赞助(首批10个公众号)
现在就开启您的创意之旅!
为鼓励创作者开启创意之旅,人间烟火在2025年第一季推出起步赞助计划,为符合条件的公众号提供一次性支持:
RM100 赞助(首批20个公众号)
RM250 赞助(首批10个公众号)
现在就开启您的创意之旅!
人间社区正式启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