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棲
一场写给自己的和解书信
山不会说话,却总在人最孤单的时候,静静聆听。或许每一座山,都是一种极为私密的邀请:邀你攀登的,不只是山,更是那条你一直迴避的内在之路。
写了这么多文字,我却从未真正写过“自己”。或许是害怕被看见,又或许,我始终觉得那个连我自己都不太愿提起的“我”,没什么值得书写的。
直到攀登神山(京那巴鲁山)那一程,在那条湿透、孤单的山径上,有个声音悄悄浮现:你该把这段写下来。
不是为了记得风景——照片足以胜任;而是为了记得那个,在雨中一步步往上、不停与自己对话的我。
我怕,终有一天会忘了那个自己。
那个对着雾中山峰说:“我已经没有人可以照顾我了”的自己;那个出发前低语:“若我失足,就让我离开吧”的自己。
这段旅程,是由我屋主路易发起的。刚听到费用时,我心里就凉了一半。说实话,真的负担不起。朋友们说可以分期慢慢还,但那时的我,连“旅行”这个念头都显得奢侈。
不知为何,我还是报了名。可能是那句“试试看吧”的念头,胜过了所有恐惧。名额需提前半年抢,如同演唱会门票;装备清单长得像无止境的购物单,还得追加四位数预算。我一度想放弃,但当有成员临时退出,路易可能得一人独爬时,我知道,我退不了了。
从年初苦撑到三月,我终于凑齐了旅费与装备。直到搭机前一刻,我仍怀疑自己:我真的能完成吗?
我们提前抵达亚庇,随即前往神山脚下。沿途司机不断说着“可以的啦”,一度让我误以为,这座东南亚最高峰,也许没那么难。
但当我站在那庞大的山影下,内心某个声音再次浮现。“人都来了,真的不试试看吗?”我回应它:“若我失足,就让我离开吧。没有人需要我,也没人能再照顾我了。”
神山静静地看着我。云层忽然散开,阳光穿透而下,彷彿祂也回应:孩子,别怕。
隔天清晨,我们正式出发。报到、托运行李、签署协议、与导游会合后,我们拍了张出发照,像是对自己宣告:旅程,开始了。
一路皆是湿滑的石梯与浓雾。从中段开始,雨就没停过。对我这个167公分、体力一般的人来说,有些阶梯得用尽全身力气才能跨过。我没余力欣赏风景,只顾着撑住每一步。
我渐渐超前,与队友拉开距离。心里的声音浮现:你不等朋友吗?你为什么这么急?我知道答案——我怕自己垫后,怕拖累别人,更怕证明自己不够好。
途中,有位男生反覆与我擦身而过,像命运安排好的节奏。我们没说话,却在休息点屡屡重逢。那熟悉的身影,成了我孤单路上的某种陪伴。
快到半山旅馆前,我再次遇见他。他主动说:“我们一起去报到吧。”那一刻,我的孤单忽然被点亮了。
他叫里斯,来自槟城。命运不只安排了重逢,还让我们住进同一间宿舍。
晚餐在下午四点半,七点就寝,凌晨一点半起床再吃夜宵,为两点半冲顶出发做准备。我心想:要不就在这里等他们回来吧?但另一个声音说:会不会拖累大家?
凌晨2:30到了,大家准备出发。而我,漏了两样关键装备:最底层的保暖衣与绒帽。本想前一晚在咖啡厅补买,但觉得只用一次太浪费,最后还是没买。只好硬着头皮上。
冷空气如针般刺入衣服。出发时,头灯像星河闪烁在黑夜的山径。我不敢抬头,只盯着脚下的绳索,对自己说:有绳子就走。
那段山径,像走进不存在于现实的隧道。黑夜里,每口呼吸都薄而冷,彷彿吸进的是未知,而非空气。思绪开始泛滥,像一场不肯散场的脑中会议。有的劝我停下,有的骂我逞强。
我想起许多人曾说:“你太用力了,该休息。”但他们不知道,那不是选择,而是我的生存方式。我太习惯咬牙维持完整,把情绪藏在沉默下,用安静扛起没人愿接手的重量。爬山,只是这种人生方式的具体化。
抵达山顶前的checkpoint,天仍未亮。这是3800米的起点,前方裸岩坡道,是所有人速度最慢的地段。仅三百米,却像三公里。
我几乎走不动。那段路,像在与过往最孤独的记忆对话。这不只是攀登,而是一场仪式——翻出羞辱、看清被否定的片段,然后放下。
心中浮现一句声音:你真的很棒了。
我想起小时候小妈笑我打羽毛球像跳芭蕾;堂哥笑我娘娘腔。那些羞辱,如今变成动力。我不是懦弱者,而是一步步走到这里的我。
几天前,中医师肯恩说我的体质适合运动,我半信半疑。但直到那一刻,我终于相信,自己不是无能的。
山顶不远,我一步步迈进。没有壮丽风景,只有呼吸与意志。
我终于明白,真正的攀登,不是对抗外在高山,而是回应内在低谷;是穿越自我怀疑,经过“没人理解的委屈”,越过那些“我不值得被爱”的念头。
我不是为了荣耀而来,而是为了那个从未被允许存在的自己。
那晚,神山没说话。但我知道,我被祂看见了。而我,也终于看见了自己。
我没告诉任何人,在接近山顶那刻,我哭了。不是因为冷或酸,而是因为我终于原谅了那个一直活得很用力的自己。
那一刻,神山的风轻轻掠过我的脸,如一种祝福。我知道,回去后人生不会因此变得容易。但我会记得这段路,记得那个湿透却不放弃的自己。
那是我,一步一步攀上的高峰。也是我,第一次真正认识自己。
最后几十米,路易看着我说:“要不我们就到那张百元纸钞上的山就好?”
我看了手錶,6:05。天色未晴,仍有不少人正从顶端缓缓下山。我说:“还来得及,我们走吧。”
那是最后一段路。眼前的大石不再铺出明确的阶梯,只能靠登山绳索缓缓攀登。我的头脑早已放空,只听见内在熟悉的声音:没事的,孩子,慢慢来。你快到了。
没有理智的计算,也没有强烈的情绪,只是,一步一步,走着。
早上6:34,我站上了4095.2米的神山之巅。那里仅是一块可容数人的岩石,风在高处无声咆哮。
我站着,不急着拍照。那一刻,脑中一片寂静。
没有欢呼,没有泪水,没有“我成功了”的振奋。只有一种深层的平静,像是一场梦,终于醒来。
约翰也到了。我们什么都没说,只各自静静地在山尖体会属于自己的时刻。
我成功了吗?或许不是。
但我知道,我走完了内心的那段长路。 那,比登顶更值得记住。
山顶,不过是一块岩石;人生亦然。真正让人动容的,从来不是我们站得多高,而是——在最孤单、最脆弱时,依然选择不放弃,依然向前的那份心意。
我曾以为,活得好就是成功,坚强就是不示弱。但神山教会我:允许自己软弱,才是真正的力量;不再逃避自己的故事,才是与人生和解的开始。
下山的路,其实比想像中还长,也更深刻。
我们7:10从山顶出发。天已放晴,阳光斜照山脊与石面,一切像梦一样清晰。这段3公里不难,只是斜,走得小心翼翼。
走着走着,植物渐渐多了,绿意替代冷冽的岩石。我放慢脚步,想保留体力应付后头更长的6公里山径。
快抵半山旅馆时,我遇见一位昨晚在山顶擦肩的年轻男子。我们边走边聊,笑说彼此的狼狈,也聊着彼此的来处,直到抵达休息站。
10:30,我们整队,准备踏上第二段下山路。谁料,刚出发,天便骤变。
雨落下来,从细丝变成倾盆,整整六公里,全程雨中前行。
雨水拍打防水外套,也泼溅在不规则的石梯上,每一步都在与滑动对峙。水流急奔而下,彷彿大自然也在催促:快些吧,离尘世不远了。
第5公里,路易的膝盖开始疼。我与约翰先行下山,肯恩因拍照渐渐落后。
又是一人行。
我低头走着,不再多想,只想快点下山。脑中只剩倒数:还有几公里?鞋子会进水吗?还要多久?
偶尔,背夫从我身旁擦肩而过,步伐稳重,像山的子民。而我,如借宿者,只能努力不让自己跌倒、不让包裹泡湿、不再怀疑“我可以吗”。
那场大雨,是神山最后的叩问。
直到远处屋顶出现,我知道,我真的快到了。
那一刻,阳光与雨交班,洒下一抹金光。风轻拂耳际,我听见一个声音温柔地说:你已经很好了,真的。
我停下脚步,抬头望了一眼——云散了一些,天亮了一角,而我,心里也亮了一角。
不是因为终点,而是因为我开始懂了:这段路,走的是山,也是自己。
我相信了,那句话。
不再需要证明,不再执着于成为谁眼中的“值得”,而是真实地承认——我一路走来,真的很好了。
我们大约在下午3:30抵达山脚的报到处,雨仍未歇。风冷透骨,让人不想久留。约翰和我早已换掉湿衣,身上只剩薄薄干衣,寒意仍不放过我们。
4:27,肯恩抵达;5:30,路易与山导也终于走下来,队伍终于齐全。
那一刻,没人多说,只彼此望了一眼,像是在确认:你也还好吧?
我们踏上回程,处理下山手续,吃了那一顿不算丰盛,却特别温热的晚餐。
那一夜,没人说想再爬一次。
我们安静地,与神山道别了。
没有隆重仪式,没有激昂语句。
只是——各自收拾湿漉漉的衣物,与那个在山里真实流淌过的自己,轻轻挥手。
而你呢? 你也有一座还没启程的山吗? 又或者,正在某段看似走不完的路上?
愿你也能在某个时刻,停下脚步,轻声问自己一句:嘿,我是不是也该和自己好好说一声:你已经很好了,真的。

本篇作品入围人间烟火年度散文奖,获得 RM50 稿酬,并有机会赢得高达 RM1000 奖金。更多详情 ≫

Featured Photo by glitterly.app on Unsplash
支持作者
喜欢这个作品?请略表心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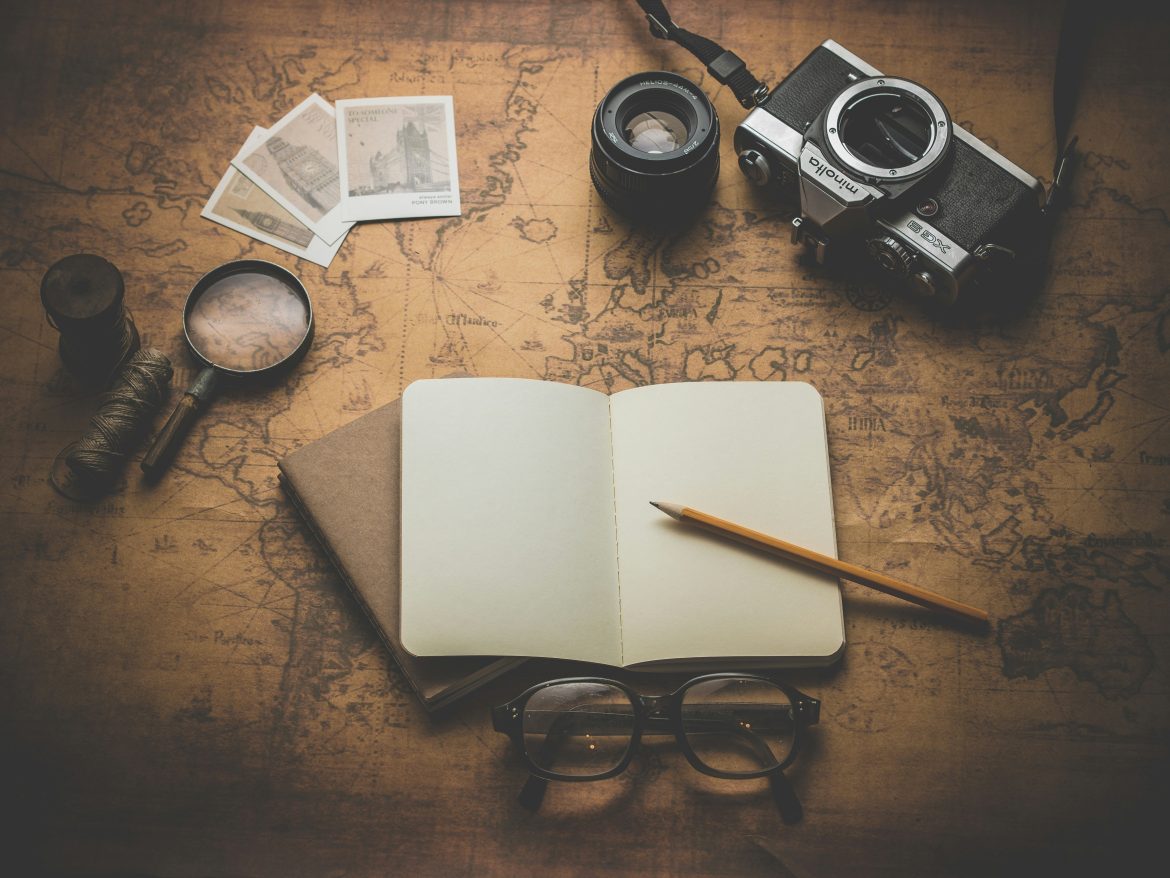 为鼓励创作者开启创意之旅,人间烟火在2025年第一季推出起步赞助计划,为符合条件的公众号提供一次性支持:
RM100 赞助(首批20个公众号)
RM250 赞助(首批10个公众号)
现在就开启您的创意之旅!
为鼓励创作者开启创意之旅,人间烟火在2025年第一季推出起步赞助计划,为符合条件的公众号提供一次性支持:
RM100 赞助(首批20个公众号)
RM250 赞助(首批10个公众号)
现在就开启您的创意之旅!
人间社区正式启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