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文学馆推荐作品
曾翎龙
有点马来高脚屋的意思,要上几级木梯才进到内里。但脏乱得多,甲板上散放着杂物,报纸,连环图,瓶瓶罐罐;墙上钉著赛马月历牌,没天花板,抬头便可望见锌片,缝缝补补。都是家里替换的,或从村里某处捡来,草草搭上。木板也是,上头钉痕处处,已不知是它们第几个家。没髹漆,就这么木然彼此叠著,有几块已经朽烂,一拳下去,应该可以破开来。从甲板罅隙往下望,可见底下泥土,怎么说也算有瓦遮头,筛漏阳光,潮湿得长出一撮撮草。好像也没地基,就四根木头柱子撑着,风雨飘摇却也相安无事,至少在记忆里屹立不倒。
这个木寮,我们俗称“寮哥仔”,建在阿公的胶园。胶园离家十哩,母亲每天骑脚车来回,这里是她第二个家。把脚车停靠木寮外,拎着麻包袋和胶刀,重复著几十年的推割生涯。我小时引以为耻,成绩册记有父母职业,母亲一栏写胶工,每次分发总是快快收起,同学以为我骄傲,不懂实情相反。然而无论多不情愿,假期总有几天,得坐上母亲脚车后座,摸黑出门,帮她收杯。也不是怕母亲辛苦,父亲的意思是:总得磨练磨练,好知寻食艰难。
那时胶水不盛行,收的是胶杯。我跟在母亲后头,她头巾上绑了盏灯,方寸之地有光,一步一步的走,一列列整齐的樛树。走几步便得停下,母亲撕开残留树身隔夜的树屎,也不浪费,都丟到袋里。胶刀抵著树身割痕,俐落的往上簌簌几声,胶汁开始冒起,一点一点很快便碰头,蜿蜒而下,流经“鸭利”落入陶杯。遇见鸭利歪了,母亲便拔下,用胶刀后柄笃笃两声,重新敲入树身。鸭利是一拱形小锌片,会割手,母亲不让我碰。我的工作是趁胶汁还没流下,一手挖入陶杯,把凝结的树屎掏出,丟进麻包袋。胶屎状似乳房,软绵绵且有弹性,我小小的手常要握不住,落地蹦跳,沾些树叶沙石。我小时便已开始追逐──想来造物奇妙,胶汁与乳汁,生活与养育,何等相似。造物者想出了两个源头,只不知为何要让树屎发臭。此臭非等閒,洗手多遍,用上肥皂酸柑,凑近鼻子一闻,总还留有余味。我原先坚持戴手套,可树屎虽已凝结但带水,趁虚而入,没两下手套便已湿淋淋,恶心且碍手。
麻包袋渐渐重了,我提得有点吃力。母亲接过,又割了几行树,才拖著麻包袋回木寮休息。打开带来的便当,多是粗叶粄和?粑,劳作后吃得特別滋味,却也小心握着塑料袋,不让食物沾手。开水盛在铝制水壺里,倒在壺盖就著喝,有金属的味道。吃饱喝足,开始下半程──另一处坡岭胶树正等着。此时已可感受阳光,清早的寒意逐渐被汗水覆盖。
回程时得把两个麻包袋一一拖上脚车后座,两条黑色厚实胶带一左一右,死命拉,压过满满麻包袋到另一头绑紧。母亲推著脚车走,我在后头看顾,不让麻包袋倒下。不晓得平时她怎么把树屎载到收胶厂。收胶厂都是穿防水黑靴的男工,印象中一直拿着长长水管到处喷水。该不是除臭?该不是。於臭无补。卸下麻包袋秤重,重量乘於当日胶价,即时付钱。不是血汗钱,是汗臭钱。
遇着收杯后隔天要上学,我总在手指处贴块胶布,言明受伤,可把手藏起。那时同学间流行一游戏,先玩剪刀石头布,赢的打人输的闪人;对立站著各自合掌,中指相抵,打人者或左或右分出一只掌,打对方掌背;闪人者可闪,但掌不能分。而打人者作状欲打,其实未必,可以喊声“切”,双掌分成十字,若此时闪人者抽掌散开,得受处罚──伸直手臂,掀袖;打人者迸起两指,“哒”一声往滑溜手肘拍下。要是够狠,不两下就红通一片。我道德教育常拿满分,不想遗臭他人,好几天不能玩。
最折腾的还是周会,立正唱完校歌后稍息,双手得握在屁股上,深怕后面的同学嗅出个所以然来。更可怜的是那双腿,小腿以上大腿以下,堪堪裤子遮不到的地方,缀满五分钱叮痕──蚊子嘴长,可隔山打牛,隔裤叮脚。偏偏男生站前女生在后,我在男生中又算长得高,一双腿无所遁形,整个周会手足无措,感觉背后有千百道目光一一聚焦,都在脚处。当中或许还包括隔壁班学校董事长之女陈美玲。我那时周而复始的心愿,便是快快昇上中学,穿长裤遮丑。
也不是没有好事。一天董事长请吃榴梿,每班分得一堆,城里来的女级任老师顾得了刀顾不了纤手下的榴梿,来回几次,短短的榴梿梗也还砍不断。我於是排众而出,刀一压一拗,便是一个榴梿开花。再难开的榴梿我也开过,这些D24或D2名种,一根汤匙便得了。结果“榴梿快刀”这名号不迳而走,和小李飞刀一般响亮。
那时我们都迷古龙金庸,每回到胶林守榴梿,都会带上几本。父亲骑摩哆,我抱着父亲哥哥抱着我,与晨早收杯心不甘情不愿不同,此时心情充满期待;午后的木寮也变得可亲,巴不得快些到达。到达了,便拿着父亲的巴冷刀,到木寮附近转个圈,也算干些活:拔拔橡树苗,砍砍拦路的枝叶。我和哥哥最喜欢砍香蕉:采收了留下无用,正好让我们试刀。一刀横劈,断不了便是内力不足。断过一截不罢休,换个人再砍,不硬,且带水,血肉之躯般真实。
拾些枝叶回来,父亲已升好了火,新鲜枝叶搭上去,煨烟驱蚊。木寮外是一片沙地,我和哥哥各端张椅子,投身江湖。父亲自有得忙──喷农药或其他,我们閒坐,只因此行主要是捡榴梿,而榴梿是黑夜之子。遇有蚊子来扰,也不扫兴,乱拍一通,好练眼力。只是拍扁的蚊子多没血,杀得不够痛快。哥哥说是杀错忠良,但有杀错没放过,刀剑无眼。看得几个回合,骨头酸了便站起来舒筋,拾根木枝,赤著脚游走,口喊刚悟得的招式,即场华山论剑。斗得正酣眼看难分胜负,弃枝改拳脚,你吼我一记蛤蟆功,我还你一记黯然销魂掌。
也拾橡胶籽──劈啪爆开,穿过树叶,簌簌有声。不纯粹为了玩,橡胶籽很快成苗,拔起来颇费力。一人捡一堆,比硬;左右手各握住一粒,合起来放到大腿内侧,对準了压下去,喀啦,碎裂的游戏。破了头的便丟进火堆,种子里有一软核,焖得出烟。如此大战数十回合,最终的胜利者拿着他的橡籽王,来回往柱子上磨擦生热,快速压到敌人手背上,像打败仗的战俘被铁片烙印。偶尔父亲也加入战围,三人混战,各自挑兵选将;总还是父亲赢的多。
入夜前通常要采山竹,当餐后甜品。我和哥哥双手捧著麻包袋在树下兜接,噗一声一串,噗一声又是一串,大珠小珠落满盘。遇有硕圆油亮的,父亲会用小刀拦腰切开,紫红汁液沾手,真是白刃子进去,红刃子出来。往山竹底部戳个小洞,穿过一根橡皮筋,洞外横根小树枝固定,再往壳里打个结,便是简单童玩。拿着橡皮筋末端转动,让山竹在地上兜圈,待橡皮筋绷紧便提起,会有美丽图案旋舞。若用上不同颜色的橡皮筋,会有纠缠的,变换的色彩。
胶园四周种了十多棵榴梿树,棵棵有名,如大石旁的叫“石头”,拿督公旁的叫“拿督公”,常生蕃薯(果肉生硬不能吃)叫“大蕃薯”。都有个性,不像名种榴梿,面目模糊。吃得多了,单看形状便能分辨;或拎着榴梿在耳旁摇,摇得出声的,应该就是“石头”。我们最喜欢吃的便是“石头”,软硬适中,甜中带一丝丝苦,果肉裹有一层薄膜,拿起不会沾手;且物以稀为贵,多是一瓣榴梿一颗肉,最多三颗,偶尔掰开,空空如也,宁缺毋滥。夜里榴梿坠地,我们听声辨位,若是“石头”那边传出,便兴冲冲带上手电筒去搜寻。若是“大蕃薯”,你推我让,谁也懒得动。奇怪的是,守榴梿这么多回,不曾戴头盔,却也不曾被榴梿砸中。每次拿着木棍在野草丛中左拨右撩,作地毯式搜查时,确也担心会中头奖;但榴梿像是长了眼睛,知道有人在它底下,不欲惊扰。更怕的是有蛇窜出,幸好蛇似乎不好榴梿滋味,不在附近流连。想来以蛇的吞食习惯,若真吞了个榴梿,来不及消化便已洞穿几个透明窟窿。倒是晚间睡觉时,得在木寮甲板上铺张草蓆,防蛇从罅隙突袭。
榴梿不怕蛇,怕大蚊鼠。大蚊鼠,小时都这么叫,我怀疑是大尾鼠的音误,应该就是松鼠。松鼠是老饕,懂得选,凡它吃过的味道不会差。每回捡得一片鼠藉,已遭破身的榴梿,总要丧气:又被糟塌。这榴梿卖不了钱,多是当场自己吃了。可恨的是松鼠贪,一粒榴梿只肯吃一瓣,有时一瓣三颗果肉只吃了一颗,许是发现不对味,又鼠过別枝,继续盗香。逼不得已,每年父亲都请枪手来杀,把芭场当靶场,一只十块,尸身都让枪手要了去,不晓得煮出的汤,有没飘着榴梿香。
松鼠可杀,人只能防。我们到胶园守榴梿,只因母亲常埋怨,山番仔会来捡。我想像中的山番仔,穿的是丁字裤,脸上还涂有油彩。但那并不真实,山番仔只是住在山下的土著,也得生活,除了皮肤黝黑,常赤著上身,一般与常人无异。有时我们到木寮守夜,山番仔会送来几串臭豆,父亲也不以为忤,与他攀谈家常,走时还回送几粒榴梿。我不解,这物物交换,也太便宜山番。父亲却说,榴梿是果王,臭豆是豆王,小看不得。也对,王者自有风范,臭豆炒虾米峇拉煎,最是惹苍蝇,和丟到垃圾桶的榴梿种子一样。
但我可不愿以此类比──若说惹苍蝇,小时茅房底下那桶屎上面,满满一层都是。说到“王”,想起周会时唱州歌,总要错唱成Durian yang mahal mulia,selamat di atas takhta;珍贵的榴梿安坐王位。橡胶更不得了,改的是国歌:Getahaku, tanah tumpahnya darahku。原先以为是土生土长,后来才知道是从南美洲移植。
后来我已久未踏足胶园,偶尔回家骑着母亲的摩哆外出,下车后把手凑近鼻子,还可嗅得橡胶令人怀念的味道。母亲改骑摩哆后,父亲在后座焊了个铁架。前阵子胶水好价,母亲总爱在我面前坐着数钱,一百块一百块地压在后脚跟,很有点自得:赚得比我还多。不晓得为什么,胶工都有著破裂的后脚跟;而且指甲边黑黑的,土地的颜色。
去年带外甥到母校,参加运动会,遇上了陈美玲。她已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竟与我外甥同班。两人讪讪的也没什么话题聊,最后她说:找天约些小学同学,去我爸的榴梿芭吃榴梿。我说好啊,始终不成行。有时在超级市场看到保鲜膜包着的榴梿,匆匆绕行。
总觉得榴梿离开了榴梿壳,便失去生命力。味道是有,已经变得恶心。所以举凡榴梿糕榴梿cendol榴梿冰淇淋,一一入不了口。小时人多,榴梿也没滥市,可以卖个好价钱。一家人围吃,不几回便已清袋,常常吃不过瘾。如今哥哥到新加坡工作,两个妹妹嫁了出去,榴梿倒是过剩了。偶尔母亲打电话来,也不知该说什么,就说:回来吃榴梿吧。
2008年12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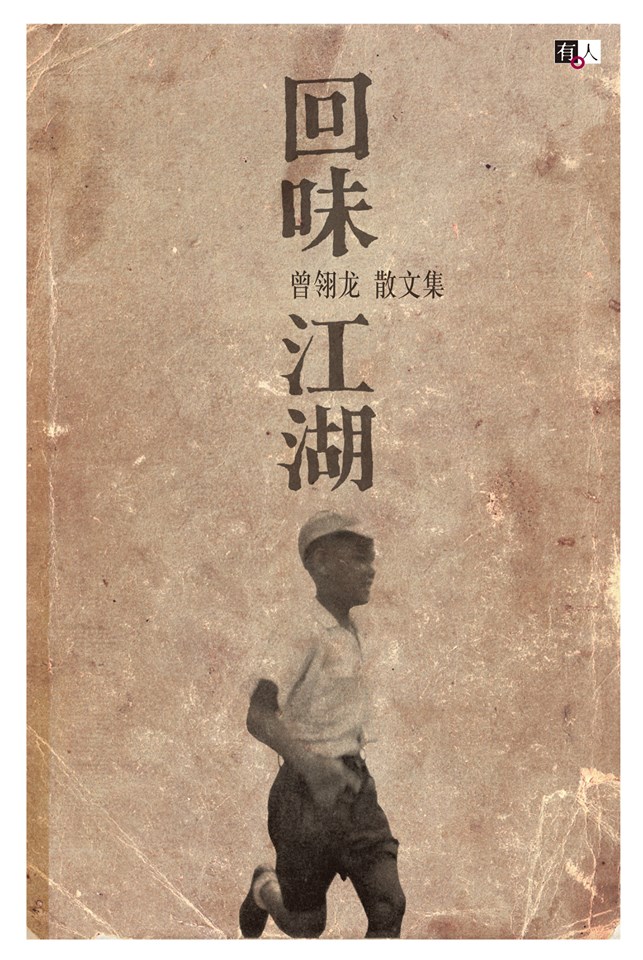
支持作者
喜欢这个作品?请略表心意。
 「人间烟火年度散文奖」,是一个旨在推广和表彰优秀散文作品的年度评选活动。过去两届的征稿活动获得热烈回响,我们宣布2025年散文奖正式开跑!
入围作品将会得到RM50稿酬并参与奖项评选,总奖金高达RM3000!
「人间烟火年度散文奖」,是一个旨在推广和表彰优秀散文作品的年度评选活动。过去两届的征稿活动获得热烈回响,我们宣布2025年散文奖正式开跑!
入围作品将会得到RM50稿酬并参与奖项评选,总奖金高达RM3000!
人间烟火年度散文奖2025开跑了!总奖金高达RM3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