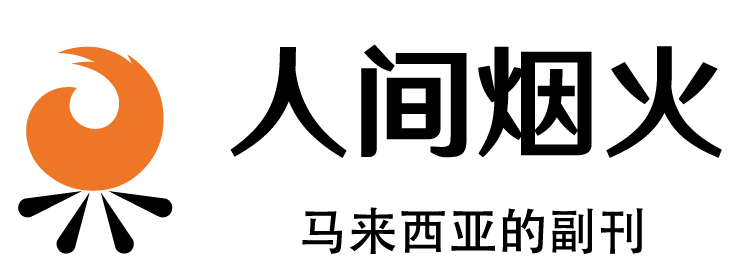刘语芳 小说
上卷:云开雾散
近下班时,乌云密布的天空,哗啦啦的下起大雨来。这下可不好了,待会儿出去还得撑伞呢!她在心里嘀咕了一下。宇生约她下班后,在她办公室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吃饭。也许是想提前把下周相恋七周年的礼物送给她吧,她推测着。
周宇生是她大学的师兄,比她年长两岁。他修的是机械工程,而她学的却是室内设计。一理一文的,不知怎的俩人竟可以走在一块。而时间飞快,这一晃,就七年了。父母催着结婚,但宇生並不急,她也觉得无所谓。一张婚纸不能保证什么, 所以就如此耽搁着。
虽然撑了一把大雨伞,但手脚不免也淋了些雨。进入小餐馆时,见到宇生已到了,而且还叫了热茶,等着她。她取出纸巾,稍微抹了手臂。坐下后,方觉得宇生神色怪怪的,有点凝重但又似有点慌张,坐立不安的感觉。
“怎么啦?” 她喝了口茶,问他。
宇生大口的吸了一口气,缺氧似的说:“以宣,再多一个半月,我就要结婚了。半年后,我不但是人夫也会为人父。”
“对不起以宣,我负了妳。” 宇生压低声音说,怕吓倒她,也许也怕临桌的客人听到。
她登大了双眼看着他,像他在用一种她听不懂的方言和她说话。他低着头,不敢看她惊慌的双眼。她不知该如何反应。忽然站起,拿了伞,急忙向门口跑去。宇生木然地坐着,没有向前追她。
老天爷像怜悯她似的,有点戏剧性的将十分钟前还是倾盆的大雨,倏然止住,只留下霏霏小雨伴着她。她懵懂的脑袋,对情变的信息接收不来。脑里一直盘问着,怎么回事,怎么可能?一直认定她与宇生终会白头偕老的,但今天那信念被宇生狠狠地否决了。
她从未为她的恋情未雨绸缪过。
她不知她是如何回到家的。接下来的日子,她混沌而过。宇生没再找她,他像人间蒸发了似的,没了踪影。七年的感情竟可以交待的如此草率,可见他的心早已离去。此情不在,他们刹那形同陌路。
傍晚的雾气很浓,白茫茫的一片,把窗外的群山全给掩盖了。迷迷蒙蒙的场景像极了她感情的前途。太阳西下后,山上的气温剧降, 冷风吹过,她不竟哆嗦一下。那冷像极了一把刀,在她心里狠狠地捅了一下,痛心刻骨。
环顾一下置身的百年英式秀茂山上的老酒店,忽觉得这洒店的腐霉味很重。闻着那陈旧的气味,她觉得晕眩。奇怪,这地方曾是他俩喜欢相约喝茶的地方。情变了,连喜欢的地方也变了样。上个月约好在此庆祝他们七年恋情周年纪念日的,但他,周宇生,却于周年纪念日的前一星期宣布了他的移情别恋。她恍然若失,精神恍惚的不知所措。从那日的宣告至今已是整整一周了,她依旧脑袋一片空白。苦苦经营的七年感情,终究还是落空了。
桌上的手机响。
“以宣,妳还独自一人上到秀茂山去?” 廿多年的老友林荟莲在电话里问她。
“既已定了这里的设施,自己也该为自己赴会的。虽不是来庆祝周年纪念日,却可在这静静的一人与过去七年恋情告别。” 她忧忧的说。
“给自己一些时间缓过去。”
“嗯”
“还有,可有考虑我前天建议的看护陪伴的短期工作? 妳辞职,无谓是想离开本地,到别的地方透透气。那份差事,我觉得很适合妳。” 荟莲鼓励着她。
“我是一名室内设计师,看护陪伴的事,我可没有经验。而且去陪伴一位年纪与我相若的忧郁男子,我真是无头绪的。再说,我现在情伤的剩半条命,自救都无能,如何去帮人?”
荟莲没放弃的再说:“我和钟靖希先生的大姐靖宁谈过的,她要找的人是位温柔安静的人,无需什么专业知识,只要能有同理心的在家陪伴着她弟弟就好。她只希望她弟能有那么一天,能把心房打开,与人沟通。妳不是也上过一年什么心理辅导的文凭课程吗?可派上用场。在钟生哪儿住下,陪陪他,再用绘画音乐等的方式给妳自己疗伤。那钟靖希先生何时有兴致和妳说话,妳才应对。听说他们祖传的生意庞大, 有制造业、地产和零售贸易等。家底丰厚,所以他家有家佣、司机的,又住在半山上,一切条件都非常适合你前去赴差,可好?”
“荟莲,我知道妳是为我好,为我安排这事。真的很感谢妳,这么多年来对我的支持。我再考虑一下,明天让妳知道。今晚想静静的度过。“
“好的,那妳也好好休息下,别太钻牛角尖了。 唉,那周宇生真是小人,一脚踏两船的混了这么多年,而妳又是一个那么没有心机的人,什么都没察觉。以前跟妳说你们性格不合,他好动而妳好静,一动一静的,如何能好好过日子。但妳却说如此互補,才是最佳拍档。七年呀,一个女子能有多少个七年去耗? 这一折腾,妳已三十了。他可真狠!算了算了,不要再提了。妳早点休息,明天我们再聊。”
“ 好的。”
盖了电话后,她眼泪如泉般泊泊而流。一星期了,她人前人后的坚强样子,此刻再也不能伪装下去了。她嚎啕大哭,哭得撕心裂肺的,像是要将过去七年的情爱恨怨哭成过去。经过一个晚上的哀痛欲绝和椎心泣血的大哭后,她似有些释然。过去的已不可挽回,宇生还斩钉切铁的说他们的情早已逝。既已成定局,就不该执着的为难自己。作了个深呼吸,她起身,拿起手机,给荟莲留了个短信:决定去赴差,何时得报到?
“妳是张以宣?喔,我是靖宁,靖希的姐姐。靖希的背景,荟莲都和妳说了吧?”电话那端传来柔柔的钟靖宁声音。
“大约说了些。宁姐若有什么要補充的,或交待的,请您向我直接说好了。”
“十二年前,他毕业后与父母同行的那个旅行,真是个劫。父母因车祸不幸丧生,而他也受了重伤,在医院躺了有半年之久。半年后,身躯之伤虽痊愈,但他心里的伤却一直带着。他因内疚自责而封闭自己,从此不言不语的。他可曾是个活泼开朗的孩子啊!他本想毕业后,承接父亲的商业王国。可惜他病了后,已不愿全权地担起父亲的庞大企业。我逼于无奈,承担起父亲的企业。他这几年虽稍有改善,每天都花些时间,和我们公司老臣子阿承了解公司业务,做些公司决策之事,但我希望他能更有所为。”
“嗯。” 她仔细地听着靖宁倾诉。
“以宣,我请妳去驻在他哪,也只想让他能感觉到有多一个人的存在,不用再那么寂寞。真希望有天,他会突然解封自己,让自己走出来。我不需妳用什么专业技巧去引导他,这会让他有压力。前两位陪伴的看护都是专才,但没有效果。妳就在那过妳自己的生活,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我只是想在他那增加些人气活动而已。
希望妳能沉住气,在那住上三到六个月吧,可好?我这个做姐姐的,也真是没什么办法了。” 靖宁说完,叹了口气。
“知道了,宁姐。我后天,星期一早上十点左右会过去的。”
“行李多吗?可要我叫司机去接妳?”
“不多,我可以坐出租车上去,没问题的。”
“那好,下周一见。”
这周末她在她的小公寓,收拾行李也大扫除,顺道也把心里不需再存的记忆心思倒出,腾出空间。
在没有四季的热带国家生活,她喜欢山上清凉的气候。而钟靖希就是住在福冈半山上的一憧别致独立别墅,自闭疗伤。周一早上,钟靖宁和家佣李婶在大门口迎接她。
“路上辛苦了,从家到这,车程也该有三个多小时吧?” 见到她,靖宁精神欢悦的问她。
“差不多四个小时。”
“累了吧?”
“还好,车上有小睡一会儿。”
她喜欢钟靖宁的凤眼瓜子脸,很有东方美。不像她的,双眼虽大,但脸型却是娃娃圆的,总是让人觉得有长不大的小孩之感。靖宁说话非常温柔慈爱,很贤静的一个人。 她希望钟靖希也能有他姐姐的脾性。
进了屋,李婶把她带到底层的客房,让她漱洗一番,再领她去客厅。客厅坐着两个人,显然的是钟氏两姐弟。靖宁见到以宣,热情的把她带到靖希的面前。靖宁如此介绍以宣: “靖希,这是张以宣,我朋友的妹妹。因工作上有些不如意,辞了工,想出外走走透透气的,我就叫她来这里小住一段日子。你帮姐姐招待以宣,好吗?”
她没想到原来她是有一个如此的原因,过来这儿小住的。可见靖希是反对聘请看护陪伴的。但她也不想驳靖宁之说,她理解靖宁爱弟心切的心情。也许让两个哀伤的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有机会互相的感化,因而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她想用平常心在这里至少度过三个月时间。三个月后,周宇生的婚礼也该完成了吧。那天他说的,他将结婚了,但新娘是他人。她以疗伤的心态过来当看护陪伴,感觉似乎不好。但荟莲已将她的背景故事告诉了靖宁,所以她也无需背负太多的歉意。
靖希长得不像姐姐,他长得高大,浓眉大眼还有一张蛮俊俏的脸,但神情却是非常的冷漠孤傲。听靖宁介绍后,他也只是冷冷地望了以宣一眼。她对他的冷淡态度不以为然,那是意料中的事。
钟大姐走后,他们俩冷漠的对峙着,只在吃午、晩餐的时候才有交集。这是靖宁交待的,她必须执行的最基本的任务。他寡言,她好静,而且她心情低落,根本提不起劲来说话,饭也吃得索然无味的。她倒是觉得亏欠了李婶,每一餐饭,都是李婶的精心佳作,但他们俩却不领情似的,速战速决的解决每一餐。偌大的饭桌,呆坐着两个失意的人,再香的饭菜也激不起一丁点的生气。
如此平凡平静的过了两个星期。她的心情也安稳了些。星期一苏医生上门给靖希复诊, 她贸然的跟着苏医生上楼到靖希的书房。靖希见她进来,脸一下刷黑了。她后知后觉的自己的唐突, 但靖宁吩咐的事,她无论如何也得交待:“苏医生,靖宁姐问靖希的早晚半颗安神药可否再减半?还有……”
“夠了,我的事不需妳插手,出去!”她话还没说完,就给靖希大声喝止了。她愣了一下,双眼张的老大的。苏医生尴尬的望了她一眼。从小到大,她从未被人如此的暴喝过。刹那间,她觉得百般委屈,加上刻意压抑的情伤忽然浮出,眼眶一下就红了。她强忍着泪水,飞快的下楼。回到自己的小房间,躺在小床上,用被把自己裹住, 像是给自己一个拥抱。“没事的,我会坚强渡过的。” 她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是唐突了,而靖希烦躁的反应又似理所当然的。她分析着当时的情况,又反复安慰自己。那晚她胃疼没吃晚饭,只喝了杯热牛奶巧克力。晚上八九点钟时,她觉得她在小房里有点憋不住气了,于是拿了吉他到前院的亭子去。
走近亭子时,方发现靖希竟坐在亭子里。她有点不知所措,想转身回屋,却听靖希说:“妳想弹曲吗?可否也让我听听?”
这是她‘上班’两个星期来,他第一次要求她做的事项。弹弹音乐,说说话,本是她的职责。既无法推卸, 唯有硬着脸皮,在委屈感未全褪去的情绪下,缓缓地弹出一首首微带哀怨的曲- 爱的罗曼斯、爱的故事、悲哀的结束、卡农D大调…..
“这些曲,以前都是弹给他听的?” 他嘴角上扬,带点冷笑的样子。
她惊讶他知道她的事。
“不是的,他不喜这类音乐,太柔了。他只喜欢电子音乐,吵杂跋扈。” 她小声的答了,觉得有点羞愧她被弃的事。
“嗯,你们並不是趣味相投?”
“没有,南辕北辙,所以现在分道扬镳。”
“觉得可惜?心痛?”
“不要谈他好吗?”
“如何自疗心里的伤,再让自己走出去?” 靖希淡淡的问。
她抬头望了他一眼,才说:“允许自己难过伤心一段日子,承认自己的痛和各种情绪问题,包容懦弱无能的自己,然后在时机成熟时,再把那些负面的情绪、感觉等放下。” 她咕噜的一口气说完。
“有效吗?”
“感觉还可以的。”
靖希忽然站起来,眼光有点迷茫的望着前方,叹了口气,他说:“我自疚自困了十二年,心里的痛把我压的有生不如死的感觉。我不能原谅自己安排的那一次的死亡旅行。若他们坚持不去,我们现在还会一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 他无比心痛惋惜的说着。
“大家都知道那是一场意外。你父母若泉下知道你现在的情况,必会心疼不已。而爱你的姐姐是如此渴望你能走出心病。一切都看你的态度了。悲剧发生了,内疚痛苦是必然的,但你疗伤的时间也太长了。该提起勇气,往前走了。”
她心里忐忑不安地说着,担心他又刹那不领情的再给她脸色看。但出乎意料的,他似乎心情平静的静默了一阵。后来竟和她聊起天来。
“妳恨他吗?” 靖希问她。
“刚开始时是恨的,恨得有点咬牙切齿。但过了几个星期后,那恨意竟然变淡了。也许刚分手后的感觉除了恨,应该还夹带着恼怒羞愧的。那种被人丢弃的感觉很不好!”
“这么快就可以平息了那激烈的感觉?还是在自欺欺人?” 靖希试探地问。
“其实冷静后,方觉得我们的感情早就变了、淡了。分了,该是对大家都好的。我始终得面对事实。想通了,就得把乱七八糟负面的情绪打包,然后逐一丢掉。一件件的丢下后,心情也慢慢的变好。”
“听起来,蛮管用的。” 他牵强笑了一下说。
她微笑着,然后鼓起勇气问他:“你也可试试?把自己的痛苦的情绪,慢慢的放下?”
空气刹那凝结了似的,让人透不过气来。
“晚了,该休息了。” 他苦涩的说。
说完,他匆匆地回屋里去,没给她正面的回应。她想也该让他有点时间消化她提出的自疗方案和设定自己放下的时间。但无论如何,今晚确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有交流,就是有影响的机会。
从那晚的小谈后,他们竟开始互动了。他早上陪她跑步,然后处理公司业务,下午看她种花、画画。温馨平静的日子,安然飘过,无声无息。
“妳用彩色铅笔画画?那不是小孩用的材料吗?” 靖希语中带笑地问她。
“是的,好像小学生才用彩笔画画的。没办法,我画画沒信心,又喜欢涂鸦,用彩笔画可以涂改。但水彩和油画却不能随意涂改,下笔时除了要有灵感驱使外,下手也得果断。我做不到。” 她自我嘲笑一番。
“其实兴趣的事,随心随意就好,无须太在意。” 她補充的说。
“喜欢画什么?” 他问。
“画云和花。天上的云,变化莫测。你可天马行空的把它们想像成任何东西,然后记下。地上的万草千花,斗色争姸的,好不热闹。”
“我还喜欢写小短文、诗词之类的小品。在每张小画上写上几个字,给于它们故事。也许有一天吧,可以出版一本小画册。”
“你可有什么兴趣?”她转头问靖希。
“雕木吧。”他说。
“雕刻需要很大的耐心,专注力也要很长。拿了一块木头后,你得好好和它沟通。看清木头的本质,木纹等,方能雕造成一件好的成品。” 他兴致盎然地说。她第一次看到他如此开心的样子。
“找一天雕个小品给我?” 她提了胆问他。
“好,” 他竟然爽快地答应了。
她有点受宠若惊。
他顿了下,好像才想起什么似的说道:“对了,每年九月中,钟氏企业会在福冈山上举办一个花农的花圃展。展出的花种该有几百种吧,一片片的花海,煞是好看。花展的票费都会捐给花农们的。妳可要參观?”
“那当然!能有眼福观看百种花簇锦攒的盛境,我哪能错过。还有两个月时间对吧?我拭目以待!” 她兴奋地答了。
看到她手足舞蹈的样子,他嘴角不禁露出罕有的温柔。
>> 中卷

支持作者
喜欢这个作品?请略表心意。
 书满季最新上架的两个内容,分别是马土土的《仇絲》长篇小说以及荷莉的童话王国带来的《我的妈呀!丁三的牙齿长了一朵花》有声书,让您畅游阅读世界的不同维度!
书满季最新上架的两个内容,分别是马土土的《仇絲》长篇小说以及荷莉的童话王国带来的《我的妈呀!丁三的牙齿长了一朵花》有声书,让您畅游阅读世界的不同维度!『书满季』引领大人进入迷人小说世界,让幼儿沉浸童话有声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