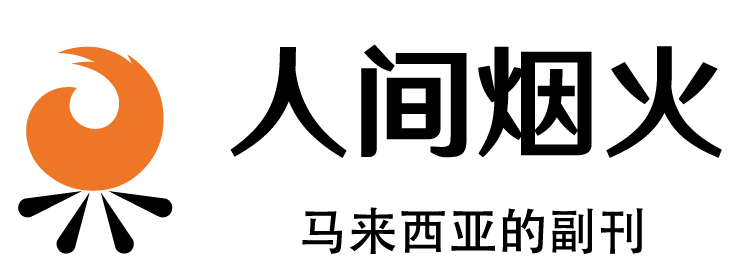节录自:人间烟火 – 种字 / 全文点击:Read More
张秀彩
组织了自己的小家庭后,回家的次数扳开十指也数得清,尽管那只是一座槟威大桥,外加一段高速公路,再来个九拐十八弯的乡间小路距离。说远,那是以码数来计;说近,却的确是争分夺秒之算。宝贵的周休二日都被耗在孩子的才艺班、补习班等各类课外活动中了,回家的归途因而变得长路漫漫,遥遥无期。每一次动身都是从紧凑的时光中挤出来的罅隙,匆匆地往,匆匆地返,形色匆匆的行脚满载着百感交集,没有一次叫我不淌泪的例外。
如赤子回归母体般澎湃激动的心,每次回家前,我会想方设法把一切平时未尽的孝道一并带回去。比如,准备各种水果糕点饼干蜜饯,就像小时候父母偶尔放纵的一次自主性选择零食那样,手推车里总是有装载不完的食物要捎回去。想着只有两位老菩萨的家里恐怕食物不足、或许日用品也欠缺,再来就是防疫的物品不知是否用罄?家庭聚会时无数次的缺席总叫我心虚,于是,非得小心翼翼地将一车又一车的不安与愧疚填满车厢才甘愿启程。孩子喜欢笑我,回娘家就像搬家……孩子,就算把全世界的奇珍异宝都搬回去,也比不上我拨冗一日的贴身相伴啊!幸运的是,外子十分孝顺,除了纵容我近乎歇斯底里的购物,他还会在一旁提点遗落了什么,而品质与价钱间,总是以前者为重。
那天又到了回家前的购物日,疯长的乡愁撩拨得我魂不守舍,结果忘了给手中的香蕉称重,队伍却已排到跟前,犹豫着放弃还是坚持,柜台的小姐撅着嘴说:“小姐,我猜你应该是面对便秘问题,但是你既然买了奇异果和木瓜,都是通便秘的良物,少一味香蕉又有何妨?就别为难我们这些小人物,你看后面还排着很长的队伍呢……”然后愈发放肆的从小声说、细声笑到倚靠着身边的助手笑得花枝乱颤。我不确定柜台小姐当天是否忘记服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她只记得自己的身份,却忽略了该有的教养。我铁青着脸怒瞪眼前讪笑的嘴脸,硬是摁着热肺里翻腾的火气,脑海里闪过了一幕熟悉的场景,当时自己的失礼叫父亲念叨了好久。
那是得知他老人家生病后的一个白天。晴天霹雳的消息,把正在午睡的我轰醒。披了件外套,我便疾奔医院。午后的医院,人潮依旧。我懊恼着泊车位的稀缺而鼓噪了满腔的怨气。最终因为姗姗来迟,仅来得及目送步履巍巍颤颤的父亲被叫去照透视镜。一扇门将我堵在了冰冷的世界以外,门外熙熙攘攘的人声沸腾,我却紧攒着拳头,目睹着护士如何粗暴的呼喝国语英语皆不灵通的父亲。
也许是一夜没睡好,也许是工作压力山大?也许是各种也许,但带着情绪工作绝对不理智,尤其是呼喝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家。看着虎背熊腰的她叉着腰,颐气指使地叽里呱啦了一大堆,老父亲佝偻着身子晕头转向地左顾右盼,冷漠的空气里人人自危,哪怕只是飘来一丝关切的眼神也欠奉。按捺不住胸腔的熊熊怒火,我推开门一头栽进了里头冷若冰霜的世界。在父亲的眼里,我就像一根救命的稻草飘然而至;而那个被戳破锐气的护士则顿时折翅敛羽,结结巴巴地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好对着我讪笑。一齣《铁公鸡斗蜈蚣》的戏码随即上演,父亲惯知我的脾气会如野火燎原般一发不可收拾,拼命地安抚我,把我推开后还不住地向护士哈腰道歉。我虽暂时偃旗息鼓,但灼灼的目光仍旧紧紧地跟随着他蹒跚的身影在里边过关斩将,那副讪笑的嘴脸与今日如出一辙。整理一番冷却下来的思绪后,猛然想起,怎么病恹恹的父亲一下子就把曾经说得溜不溜嘴的国语全忘光了?舍弃了香蕉,我狠狠地瞟了柜台小姐一眼,拎起环保袋离开。身后响起她的高分贝的惊呼,想来她真是三八,没看过女人对她竖起中指!
那天从医院回家的路上,恰巧遇到了下班的车龙,父亲碎碎念了好几个小时。具体说了什么,我没有努力地记下,因为心里铺天盖地的都是医生凝重的神情和严肃的结论。急切地想要厘清医生口中那些艰涩拗口的医学词汇——静脉瘤?血管瘤?手术风险多大?如何进行?后遗症?手术费用?一颗颗问号衔接成一串无形的项链,紧箍着咽喉,清了无数次喉咙却无法串出一个安慰的句子来。话语失重,我只记得当时的自己用沉默来回应父亲有意无意的掩饰悲伤。他责备我擅闯的无礼、与人对峙的幼稚、不体谅、不尊重……可是他自己却只字不提医生的话。我想他是明了的,因为医生照了图、画了像,还巨细靡遗地向我们讲解手术的方式。听不懂外星语,总看得清图画吧?此时此刻,我们只是心照不宣啊!
在鹑衣百结、饘粥不继的童年里,那年八岁的父亲丧母,提早来到的苦难剥夺了他上学的机会。为了底下一群楼梯阶的弟妹们,父亲放下书包,挑起扁担,也挑起了身为长子长兄一世的重担。赤膊赤足的稚龄小儿,穿街过巷卖豆花、卖糕点,吆喝着自己的幸与不幸。幸的是自己犹有祖父母和父亲健在,尽管年迈,仍能制作豆花与糕点,尚可照顾家中嗷嗷待哺的几个弟妹;不幸的是未曾耽溺的母爱及早消逝,又一波噩运毫无预兆地降临,带走了意外溺水的妹妹,叫他捶胸顿足,吁天无门。自责于愧对骤逝的母亲,自责于没当好大哥的责任,摞在肩上的担子千斤重,他的童年盛满了一钵钵血泪,尽是一幅怆恻的黑白画面。磨难让他迫不及待地长大,濡血自疗的日子不容许拖延太久,他把十四岁长成了十岁。
发育不良的体格除了一身硬气,皮囊下包裹的是无多余脂肪的筋骨。而偏偏是这副不向恶劣环境低头的傲骨,支撑着他毅然投奔怒海。旱鸭子的父亲原本拒水惧水,妹妹的意外阴影如影随形,但为了家计,硬着头皮跟随爷爷撑起橹槁。腥膻的海风拨乱了头顶黄毛,却抖不掉他泱泱尘世的哀愁。泳术在灌了不少海水后终于掌握,父子兵从此在波涛汹涌的万顷烟波中浮沉不定。广袤无垠的碧海虽然给予一家温饱,却也多次警示,贪得无厌的人们啊,终将血债血还。然而,他并非生性彪悍好斗,非得对虾兵蟹将赶尽杀绝,父亲眼里只有一家十余口的重担,每一趟航程都是锱铢必较的算计。
翻滚的潮汐曾经两度卷走了船只,没收了渔获,也同时将父子俩抖落在茫茫大海中。不住咆哮搏突的暗涌领了海龙王的令牌,拖着迤逦的浪花将他们带到了龙宫。瑰丽的蝠鲼夹道展翅相送,一场喧阗动地的海底飨宴却因他们的八字欠斤缺两而被拒于门外。本以为此是生命崦嵫之处,没料到却奏不起挽歌,当同行们搜索了一日一夜仍一无所获时,料想不到最后却在海面上看见被完璧归赵的父子俩。有人说是天可怜见,侥幸逃过劫数;也有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在父亲的心底,无论是福星高照抑或是来自海底的一场下马威,所有的恶业将会有结果的一天。到头来这一身难逃那一日啊!于是,他毅然决然地遵循曾祖母的训斥,卸下了渔网,也从此洗净了一双血腥的手。
爷爷归西后,父母亲竭尽所能把耆龄的曾祖父母安然地颐养天年到福寿全归。家境仍旧一贫二白,但是孝行却抹亮了门风,是村里数一数二有口皆碑的寒门子弟。熬大了弟妹,我们一群兄弟姐妹又排着队伍加入了父母人生的版图。父亲转行后,摸索着经商。虽然年幼失学,但他骨子里的勤奋与好学让他很快就迎头赶上。我这个小“秀才”就是他的小老师。每天下午,父亲弓肩缩背地挨着我坐,手上捧着袖珍词典,让我教他发音。那年,他已然迈入四十岁,不惑之年却仍在唇齿舌颚的碰撞中迷惑。那些本来各就各位的字母何以调换了位置就代表着不同的意思?而那些代表着一个意思的词汇何以在不同的语境又有截然不同的含义?从数字到颜色、从身体部位到服装打扮,所有的词汇都涂满了他自己才读懂的方言代号。多少个挑灯夜读的晚上,我们借着荧荧如豆的微光,为奔赴各自的疆场而努力?我也记不清了,但在回忆里,它却是一段属于我俩温馨且难以磨灭的童年印象。
当父亲能把袖珍词典倒背如流时,他胆粗粗地把电单车执照也考了回来。尔后,伟岸的身影单枪匹马地穿梭在乡间纵横交错的田垄阡陌,深入巫裔同胞的畛域,兜售各种货品,为交通不便利的马来甘榜捎去丁点来自外界的摩登气息。从鸡同鸭讲到比手划脚,到最后可以对答如流甚至嚼着舌根说起土语,父亲用他的坚毅化腐朽为传奇,光是这点已足以让大家刮目相看。第一桶金子在那时候积攒了下来。随后,买了货车,再后来,单变双、双变三……货车的数量逐年日增。一个目不识丁的乡下人大器晚成,拉住国家经济起飞的尾巴,成就了自己的商业帝国。这事,一直是父亲心底的骄傲,身为晚辈,我们与有荣焉。
善良与宽容一直都是父亲的代名词。中一那年,我在批发市场上认出了秘密兼职的生活技能老师,她竖起手指摆在唇边,像干物生噎那样,我把差点冲口而出的“老师”咽了下去。从那天开始,我原本够不着及格边缘的厨艺、裁缝技巧、电子工艺和木工全都顺利的过五关斩六将,拜老师所赐,那是我们之间点不破的谜。老师总是私下赞扬父亲的品格,我知道的,父亲同情她孤儿寡母,不但货物半卖半送,还宽容她无限期地慢慢摊还债务。这对一个丈夫骤逝,却仍得应付债台高筑的女人而言,父亲没有在商言商,反而跨越肤色宗教的藩篱,伸出的援手足以将她与孩子扯离泥沼。当然,父亲的手也伸向社团、宫庙、学府、慈善中心等。他筚路蓝缕地走了过来,却也遍植婷婷芙蕖,一生伴随暗香浮动,以致晚年经历多次生死攸关的大劫皆可如悟道的行者般笑着醒来。
像一只终年缀网的劳蛛,在记载人生盈亏的帐簿上,父亲终究还是预支了健康的资粮。当身子骨被癌急速啃噬殆尽之际,医生的疏忽竟然造成他的输尿管阻塞,父亲悄悄地把自己迁入厕所里,哗啦哗啦的冲水声无的放矢地叫嚣着他难以启齿的滴答滴答。而身为子女,我们竟然浑然不知!对于这场原本只是截取部分组织去化验的小手术所引发的失误,父亲扛下了所有的苦痛。白天的他不吭一声,只有辗转反侧的黑夜里,禁不住肿胀的痛楚,呻吟声才会不经意地嘣出口来。后来,我们兄弟姐妹遍寻各地中西医甚至偏方,才在贵人相助下盼到一线曙光。然而,拨云见日之际,接踵而来的噩耗又如乌云影翳覆盖大地。化验的结果不是当初天真的念想,冤亲债主敲锣打鼓地唤着纳命来,啊!
萎靡困顿的父亲蜷缩在床上,隆起的被单里裹着一个不该犯的过失。期待着疏浚后的小河翻腾奔流,汇聚成江海,大家都对翌日的手术充满着无限的憧憬,但也同时害怕无法预知的万一,狭小的病房里,挤满了被点穴消音的我们。诡异的是,中五那年的事却在静默的空气里倒带重演。画面里,埋首于历史笔记的我,在抬起头的电光火石刹那,瞥见了石缝间一条朝我吐信的小蛇,便大呼小叫地把父亲招来。小蛇惊慌失措地退了进去,眼明手快的父亲当机立断就铲起墙角剩余的水泥,就地糊了起来,三两下功夫便把石缝填平。我惊魂未定地说:“爸,小蛇会死吗?”父亲说:“不必担心,它很聪明,会从另外一边缝隙逃跑嘛!”是啊,一墙之隔的邻家那里杂草丛生,小蛇应该知道此路不通,另劈后路吧?若干年后想起,床上腹大如锣的父亲,阻滞不通的输尿管怕是缠绕着一场无法轮回往返的恨吧?那一夜,冷汗涔涔的我坐在床沿,诵了一夜的经咒,赎我假借父亲之手的罪,赎我当初不懂因果之罪,再赎我无法代父受过之罪。无奈,在逆风斗雨中匍匐前行的,仍旧只有父亲孤单的身影。
看着昂藏七尺的父亲躺成一个痛苦的疾病符号,手上的筹码所剩无几,很长一段时间,愁云密布笼罩着家里每个犄角旮旯。然而,直觉告诉我,父亲终究会是个有福之人。一如我所料,父亲不但没有埋怨失误的医生,反而感谢他的及时化验,才知道余生已在倒数。宽宏的胸襟让他无时无刻不在感恩遭遇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在病榻上,知悉了我的积蓄被朋友偷龙转凤,他淡淡地安慰着我:“也许她实在走投无路才这样,提告的事就免了吧,虽然教训有点贵。”那人失婚失业,满腹油脂蜜膏地接近我,虽说钱财身外物,但毕竟不是小数目,所以心难免戚戚焉。朋友以利相交,利尽则散,虽则我从此两袖清风,但接受并放下后,换来六根清净,仔细反思,学父亲宽大为怀倒也不坏啊!
暮年乱了套,父亲却未一蹶不振。反之,他积极配合医生,在五脏六腑的取舍间,不做丝毫犹豫。他打趣的说,自己也赶上潮流,在身上做一番断舍离,就当去芜存菁好了。暮鼓晨钟里,艰涩拗口的梵文到了他口里,句句幻化成安抚人心的暖言慰喻。当顿悟了无常,父亲足下的每一踱步都走得坦然并踏实。老家中,母亲一直称职地扮演着陪伴的角色。也曾同甘共苦,也曾共享富贵,此时此刻,携手相伴的仍旧是当年巧笑倩盈的眉眼。
每一趟从娘家启程的回航,背后两双慈目的护送就像菩萨摄下的大毫相光,暖风春阳地默默护佑我一生。婆娑的泪眼总叫我望不清父母朦胧的远影,但我汩汩流动的骨血之中早已嵌入两老殷殷的叮嘱。于是,虽然口中嚷着举棋不定的归期,但胸口已默默印刻一个确切的年月日。
云卷云舒,年华去留无声。当你纠结着何时萌出一绺银丝时,别忘了家中父母早已白发皤然。父母之恩昊天罔极,趁双亲健在,多回家看看吧!
 我一直都在努力折叠往生莲花,每一片花瓣都承载着我对已故至亲的思念。每逢初一、十五时,往生莲花都会随着金银纸一起焚化,烟熏袅袅,仿佛就在向上天传递我偷偷放在花芯里的心声。那时那刻,我不再是一个理性的大人,而如同小男孩般,希望天堂会有WiFi,能够让对方接收我的讯息,也希望天堂会有信箱,能够让对方收到我的祝福。一 芊函
我一直都在努力折叠往生莲花,每一片花瓣都承载着我对已故至亲的思念。每逢初一、十五时,往生莲花都会随着金银纸一起焚化,烟熏袅袅,仿佛就在向上天传递我偷偷放在花芯里的心声。那时那刻,我不再是一个理性的大人,而如同小男孩般,希望天堂会有WiFi,能够让对方接收我的讯息,也希望天堂会有信箱,能够让对方收到我的祝福。一 芊函以爱之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