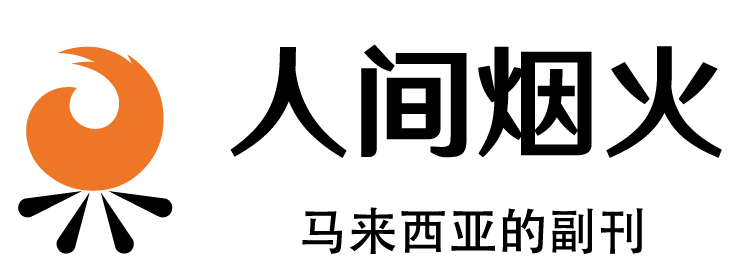金睿瑜
大学学院的图书馆,是我毕业后最想念的地方。与其说那里承载了我的独自悲欢,不如说它记载了我们三位的友情成长史。
相较于其他大学,我学校的图书馆显得窄小。图书馆坐落于二楼,放眼望去估计有二十个开放书柜。其中的三分之一是英文藏书,三分之二是中文藏书。那里的藏书不多,每位学生的借书限额只有四本书,一次可以借两个星期。这种限制对念中文系的我们是一种局限,因为系上老师的作业要求是至少四本参考书目,于是图书馆几乎成为我们每天的打卡圣地。
当时,我和朋友G和M几乎每天利用课前、课后或午休时间冲去图书馆。虽然每天过得劳劳碌碌,却成为彼此狼狈中的欢乐泉源。从图书馆夺门而入的那一刻,我们直奔文学区的其中两排开放书柜,随即席地而坐,三个女生依靠柜子喘气。也许我们活得过于潇洒,无计形象之言,在书柜前或蹲或坐。虽然我们每天重复说放纵自己,却在隔天准时到图书馆报到。于是,每天图书馆的书柜便藏匿了三个女生的身影,从而留下一箩筐的找书趣事。
偶尔,我们仨便沿着直径,往图书馆的茶室走去。记忆中,图书馆的茶室采用日式极简风的设计,里头摆了四张木质小茶几,铺了木板,外面隔了一扇门。正因茶室是一个隔间,进门前需要脱鞋,于是茶室成为图书馆里最冷的小角落,我们经常在里边“抱团取暖”。倘若没有其他同学,我们会卧在地板谈未来、聊心事、思考人生。还记得吗?我们因为一个突发的念想,在茶室里策划了一次说走就走的云顶之旅。
茶室的对面是红点书区。顾名思义,红点书区的书本无法被学生借出。红点书区的书本以马华文学及本土研究史料居多。红点书区不比茶室宽敞,只有几张桌椅,自认初老的我们蹲着翻阅资料时,经常腰酸背痛,互相捶背。
再往里面走,便是图书馆的自习区。通常,我们仨的到访都为这个区域静默制造聒噪声。虽然我们曾在案前伪装努力复习或写报告,但更多时候,我们都在谈天。即使同一时间在自习区的学生太多,抑或被图书馆管理员逮着而无法说话,我们也不约而同打开微信群聊,轮流在群组里轰炸信息一番。考试前一周才是我们整个学期里最认真的时段。我们在各自的自习桌前戴上耳机复习。我们的耳机里各有各的世界,但我们互相监督,彼此鼓励。
回想那时的我们,经常埋怨学校的图书馆藏书不够用,借书证的数量太少,但是这个狭小的地方“挤”满了我们三个人的故事。图书馆,沙雕姐妹斋堂的成立地。我们每天相聚于此,亦在此经历了一次分离。
2020年3月17日,行动管制令颁布前一天,当时正值学期长假的我们从各自的家乡飞奔到学校图书馆,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在图书馆相聚。彼时的我们适才完成文凭班毕业论文开题,原本以为四月开学后才撰写毕业论文。然而,一场疫情加速了我们分离的速度。我们第一次看见彼此戴口罩的样子,匆匆挑选毕业论文的参考书目,然后各自回家。那回的图书馆之约,少了哗然,多了离别的感伤。
疫情开放后,与我同行的G和M飞往台湾升学,唯我依然留在原地。我独自站在图书馆的书柜前翻书、找书,不再看见两张最熟悉的脸庞,我也不愿在图书馆的茶室或自习区多加逗留。本科生涯的最后阶段,显得落寞孤单。不知道远方的她们,大学图书馆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把后疫情时期的寒暄,留在大学学院的图书馆,待重逢时娓娓道来。
作者就读于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文系。
校园故事:欢迎投稿,提供稿酬。前往 ≫

Featured Photo by Becca Tapert on Unsplash
支持作者
喜欢这个作品?请略表心意。